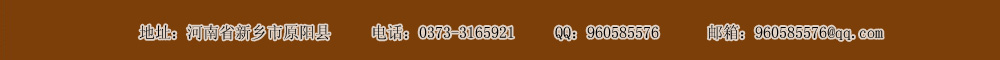医理讲堂傅延龄运用经方辨治消化系疾病
导读
傅延龄教授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庭训,曾就读于湖北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师从伤寒名家李培生教授和刘渡舟教授,为刘渡舟教授的学术继承人,是我国少有的既有家学,医院校教育与培养,且接受了传统师承教育的中医专家。傅延龄教授从医30年,擅长应用经方治疗内科疑难病症,尤其对于消化系疾病的治疗有较丰富的经验。笔者曾有幸跟随傅延龄教授学习,现将其运用经方辨治消化系疾病经验介绍如下。(策划编辑/秦丹责任编辑/王钧石)
3.析病机
抓主症是治本之法,是辨证施治与专病专方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但由于经方所述之主症往往不言病机,故分析病证的寒热虚实是后世医家必做的功课。如对于寒热病机的辨析,老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辨别胃肠寒热的方法,归纳为寒性脉症和热性脉症,其中既有对传统经验的继承,亦有其独特的创见。寒性脉症可见:面呈寒色,声低气怯,疲惫少力,懒动,纳差,胃中停水感,口淡不渴,口气无明显异常,大便清利,小便清利,手足清冷、恶寒喜暖;脉象呈阴脉特征,如细、迟、缓、弱、小、沉等;舌淡苔白;镜下胃黏膜苍白、水肿、糜烂、色白等。热性脉症可见:面呈热色,声高气壮,烦燥多动,食欲不减,反酸,烧心,口苦,或口燥渴,口气臭浊,大便臭秽、黏滞不爽,小便黄、短、涩,手足温,或恶热喜凉,脉象呈阳脉特征,如大、数、滑、浮、实等;舌红苔黄,舌面唾液凝聚线;镜下胃黏膜充血、出血、糜烂色红等。根据上述所见,如果寒性脉症和热性脉症同时出现在一个病例,如热还寒,如寒还热,错综复杂,此病症便是寒热错杂性病症。
对于虚实的辨析,老师亦有较为成熟的认识。从脉症辨虚实:如虚证的指征包括:面无热色,面色萎黄、白,舌色淡,脉软、细、弱,形气不足,这些脉和症均提示应注重补益。它们的存在不仅是局部的现象,也是全身状况在局部的反映。一般而言,这些征象说明整个机体的修复与再生功能都是相对低下的,应该补而助之。反之则为实证。从病理辨虚实: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以胃黏膜固有腺体萎缩为病变特征,却往往多伴随充血、水肿、糜烂等炎性病变。腺体萎缩是正气虚弱的表现,而充血、水肿、糜烂等炎性病变在中医学看来则属于湿浊、火热、凝寒、瘀血、水饮、气滞、宿食等邪实现象。
老师强调“症”具有表象反映性,提倡表象的准确描述,主张研究表象的发生机理及表象与表象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些研究将使中医走向深入。在消化系疾病的辨证中,老师特别强调探求症状机理,明确病变实质,使治疗立足根本,更有针对性,使运用经方辨治消化系疾病走向深入。如对心下痞这一症状,老师认为这个症状发生的机理可能包括3个方面:一是胃黏膜病变,如炎性病变,或溃疡性病变,胃黏膜充血、水肿、糜烂,病变部位神经末梢受到刺激,使患者产生心下痞满感觉;二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胃壁肌肉张力异常,如胃壁弛缓或胃壁张力过高,胃动力不足,胃排空减慢,由此导致心下痞满;三是胃幽门处机械性阻塞,如幽门痉挛,或幽门炎症、充血、水肿,胃排空障碍,导致心下痞满。故在临床上对于心下痞的患者,应辨清是炎症所致还是溃疡所致,或兼而有之;是胃壁弛缓还是张力过高,是否存在机械性梗阻等,因为针对上述病变所采用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4.明治法,选方药,定药量
傅老师在用经方治疗消化系疾病时,常常讲“古方以不加减为贵”,因经方配伍严谨,法度森严,若辨证准确,往往有覆杯而起之效,后学尤其是初学者应多守方,忌胡乱加减。但考虑到临床病证的复杂性,当经方的运用渐入佳境时,又不能死守,还需结合病情之轻重、兼夹以及患者体质等予以适当调整,如临床见到大柴胡汤证的患者,但又确属年老体虚,或见不足之形色者,老师又适量用党参益气扶中。
在抓住主症,初选经方的同时,必须明确病证的寒热虚实,使方药更加切合病机,并要注意药物的用量。
(1)温与清
消化系疾病纯寒者有之,一派热象者亦可见到。但大多数患者病变是以寒热错杂为主,临床辨证时,要仔细分析,权衡寒热轻重比例,是热多寒少,还是寒多热少,抑或寒热等同,然后根据寒热的比例决定寒热药的用量。老师用药多从仲景常用之芩、连、栀、姜、夏、参、草诸物中选择。对于目前临床上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的病例,倾向于用苦寒清热解毒之品的情况,老师以半夏泻心汤类方为例说明,认为这样其实是不可取的。药理学研究[2]证明,该类方具有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完全来源于黄芩、黄连,而是与方中任何一种药物都有密切关系。所以老师认为临床见症若没有过多的热气,不要因为幽门螺杆菌阳性,盲目地加大苦寒药物的用量,或另外大量加入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否则会损伤脾胃气,于病无补。
对于仲景原著中规定的剂量,老师认为其只是基本的剂量,只可视为参考用量。在临床具体应用时,不必拘泥,也不可拘泥,因为临床病例的寒热比例是不同的。如果热气较多,寒气较少,则芩、连用量宜大,而姜、夏、参、草的用量要适当减少。反之,如果寒气较多,热气较少,则姜、夏、参、草的用量宜大,而芩、连用量应适当减少。老师用黄连,有时仅用1-3g,而有时却用至10-12g;黄芩少则6-8g,多则12-15g,甚至20g;姜、夏、参、草用量在6-15g的范围内选择。总之,寒热药的应用一定要从辨证中细求。
(2)补与泻
外证的热象、实证,加之病变局部的炎性病变(充血、水肿、糜烂等),在中医学看来属于湿浊、火热、凝寒、瘀血、水饮、气滞、宿食等邪实现象。根据这一认识,在抑制消化道黏膜的炎症时,要根据具体病情,分别应用祛湿、清热、散寒、化瘀、利水、行气、消食等方法。老师习惯应用芩、连、姜、夏、枳、芍、栀等物,增损剂量,随证治之。药物不多,但一药多效,对其病变的作用可谓面面俱到。无论病变黏膜炎症的原因是什么,都能产生较好的治疗效果。
外证的虚象,局部病变如腺体萎缩、黏膜缺血淡白等均为正气虚弱的表现,应以扶正为法。桂枝汤、理中汤、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及四君、益胃、归脾等方剂,都可以随证选用。老师在临床上习惯应用仲景常用之黄芪、党参、甘草、白术、当归、地黄等。根据老师的经验,黄芪、党参、白术、甘草、当归、地黄等药所组成的方剂具有非特异性的促组织再生作用,对机体所有组织细胞,包括皮肤、肌肉、神经、骨质、黏膜、血细胞等,均具有促生长、促再生作用。
虚实夹杂证,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既存在腺体萎缩又有炎性病变,此时要结合患者全身情况综合考虑虚实双方的力量,既不要被可能存在的湿、热、瘀等邪实的标象所迷惑,弃补不用,又不要一味蛮补,因为泻实有时即可起到类似于补虚的作用,如同蒲辅周先生所言“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
对于补药的用量,傅老师强调使用补药一定要注意剂量,既要注意其绝对剂量,又要注意其相对剂量。古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是有一定道理的。某处方中用没用某种药物,这只是决定疗效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是否足量,且用量是否恰当。应补气的情况下,黄芪仅10g,甘草仅3g,杯水车薪,何用之有?尤其对于甘草,老师认为对于脾虚型的慢性腹泻一定要重用,虚甚者可以用到30g甚至更多。甘草缓中补虚,止泻作用甚强,这一点可以从仲景半夏泻心汤到甘草泻心汤的变化中看出。甘草泻心汤证患者“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泻利可谓重矣,仲景加重的药物是甘草,而且以之命方名,即是在强调这一点。另外,某些补药若兼二任,用量也应该较大,如甘草、大枣,当既需要二者发挥健脾和胃的作用,又需要它们发挥“和诸药”的作用时,用量应该大,如大枣的用量,老师参考仲景的用量,常用到30g。而且老师强调“和诸药”对消化系疾病的意义尤其大,可以减弱汤药的苦味,使胃能受药。
对于补药的监制,傅老师认为在用补益药物时,参、芪、术、草、归、地等物若用之不当,有可能导致“补而致壅”或“气增而热”等副作用,所以应用监制药物亦很重要。要谙熟配伍之妙,选用适当的药物监制之,方能避免患者服药后的不适反应。仲景用苓制术,东垣用橘制芪,这些经验是值得后世学习和借鉴的。傅老师在用参、芪、术、草时,若虑其壅气,常佐用香、砂、枳、朴等味。另外,妥善处理兼夹邪气也能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有湿祛湿,有水消水,有热清热,有寒散寒,补药之用,何弊之有。
专家介绍
傅延龄教授、主任医师
首届国家级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临床、教学和科研,具30多年医疗经验,擅治多种内、妇、儿科疾病,如急、慢性发热,咳喘;食道、胃肠、肝胆、胰腺疾病,如食道炎、胃炎、肝硬化、胰腺炎、消化道肿瘤等;肾病,心脏病;月经病及带下、不孕,慢性湿疹、皮炎、痤疮,自体免疫性疾病,腰腿痛等各种慢性疼痛、眩晕、耳鸣聋、失眠、虚弱、便秘、浮肿等。精于脉诊和望诊,善用经方,疗效卓著。
门诊时间:周一下午、周四晚上
挂号费:元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来源:
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