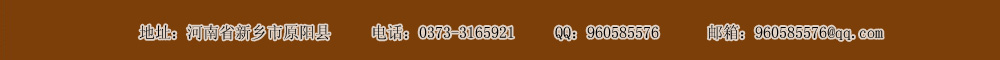专题医院和我们的城市一起成长
原载年《文汇报》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当时小儿常见、多发的感冒、腹泻等病,在家长之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话:“医院配一两瓶红、绿药水,一两天就好了。”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这话真是“老百姓的语言”,不专业、不科学;但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人民群众的认同与信任。专业与科学所追求的,不正是这个么?医院依然如此,虽然它已是一个各科室“全面发展”的巨人。医院与患者、医院与社区、医院与城市的和谐互动,浓缩在这所新医院半个世纪的经历中……
无须讳言,上海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数一数二。而其中最耀眼的光芒,无疑是由位于“塔尖”医院放射出来的。上海的“三甲”,医院医院的传统,有上百年的院史,亦不乏以两院院士为“镇院之宝”。若以这样的“家世”来考察,医院在上海滩的资历真的不算深。
但在它的故事里,仍然有别人难以复制的意义——
它是解放后上海自行设计、建造医院。从诞生到成长,医院经历的种种变迁,都与新上海的发展紧密相连。医院与城市在这半个世纪中一起迈出的每一步,都值得珍视与铭记。
“诞生在火红的年代”
“你诞生在火红的年代,你沐浴着阳光站起来……”《新华之歌》这样唱道。
年,上海高等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按照当时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要求,由上海第二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院内建立了儿科医学系的教学基地。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基地所属的病区、教室、学生宿舍和场地等都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扩建新院的工作很快就成为当务之急。
新医院最后落户于上海市产业工人最集中的杨浦区,这和它已故的首任院长曹裕丰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曹裕丰(-),男,浙江宁波人,泌尿外科专家,三级教授,九三学社成员。年获圣约翰大学博士学位,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科硕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曹教授在圣约翰大学发起组织义勇军。抗战医院,并设法为苏区购置药品器材,为治疗伤病员创造条件。解放前后先后担任上医院住院医师、医院泌尿科主任、医院院长兼泌尿科主任、医院泌医院、医院、医院院长兼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副主任等职务,为医院和儿科教学基地的创建和壮大做出了贡献。
当时,医院筹建组曾在市中心多处觅址,先后考虑过锦江饭店、衡山饭店及上海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周边的一些地点,都最终未果。但与此同时,时任二医儿科副主任、新医院筹建组组长的曹裕丰却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要为工人服务,就要站得高,看得远,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到人口众多的地区去。”
他提出,杨浦区人口多,产业工人更多,是我们发展和服务的方向。上海第二医学院领导和儿科系领导集体支持曹裕丰的意见。选址的眼光因此投向了上海的东北角,医院的建设重合到了一起——当时的上海共有18个区,今日的杨浦区主要是由当年的杨浦、榆林两区合并而成,五角场、邯郸路一带则是从北郊区划过来的。
医院的创业充满了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气氛。医护人员既治病救人,又参与基本建设;白天门急诊,晚上还有义务劳动。因为上级拨给的预算有限,院内的中医科门诊、中药库房、实验室、动物房、技工间、木工间、浴室、废品间、堆煤场等等都由员工自觅材料、自行搭建,虽然造得简陋,却实实在在地管用了好多年。院内近七千平方米的水泥路面,也是员工们亲手铺设的——上班是穿白大褂的,下班后换一身衣服就来学着挖路基、铺石子、运黄沙、拌水泥。中心大道和通向儿科大楼的水泥路拓宽工程,靠的还是挑灯夜战。老医生们回忆说,那时候的晚上,铁锹拍打路面的声音和欢畅劳动的号子交汇成一片,繁忙而热烈。晚上11点钟,食堂为每人备上一碗菜泡饭,吃完后各自回家,第二天照常准时上班。
在建院之初,医院的医务人员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从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的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后医院)等陆续调入的,是来自全市四面八方的“空降兵”。
为了请来名医,曹裕丰也一度伤透了脑筋,跑断了腿。
医院位于杨浦区的“下只角”,偏远在市区一隅,交通不便,不少调入的人员有顾虑,不肯来报到。曹裕丰就逐一登门拜访,做思想工作,发出真诚的邀请。他为邀请一位知名专家,曾先后九次亲自登门做工作,对方最终被曹裕丰的真情所感动,不仅自己来了,还动员了其他四名骨干医师一起前来。
第一批报到的专家有妇产科田雪萍、外科何尚志、胸外科梁其琛、内科李丕光、肺科朱尔梅、儿内科齐家仪、耳鼻咽喉科毛承樾、眼科曹福康、中医科丁济南、放射科朱大成、病理科陈忠华、小儿外科杨永康等,他们医院按时顺利开业。
与工业区的“鱼水情”
也有人说医院“小”,但也许,只是它的病人平均年龄小。
这医院,大人小孩的病都看,但最出名的,还是儿科。每天,总有三千个小孩在这里进出。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当时小儿常见、多发的感冒、腹泻等病,在家长之间就广泛流传着:“医院配一两瓶红、绿药水,一两天就好了。”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这话真是“老百姓的语言”,不专业、不科学;但是,它所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认同与信任。专业与科学所追求的,不正是这个么?
医院落户在上海最大的工业区,直接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一开业就和八十多个工厂建立起了劳保制度,医院送来的可不光是病人——
小儿心胸外科的手术基础,离不开上海医疗机械厂生产的第一台国产的毫安摄片造型机。营口路医疗仪器厂生产的第一台直线加速器、医疗机械厂的第一台电子加速器、第一台脑CT都送进了医院,医院一分钱。上海电表厂有位工人因脑外伤被送进医院,老院长曹裕丰亲自坐镇,指挥各科尽全力抢救。患者最后虽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但这件事感动了上海电表厂的全体职工,结果他们专门为医院研制生产了第一台国产的体外循环小儿人工心肺机。
医院的吴守义教授是我国小儿骨科的创始人,他为治疗儿童先天性髋脱位而潜心研制的专用器械“鹅颈钉”,至今仍在临床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小儿骨科初创时期,都是用成人的手术器械来为患儿开刀,既给医生带来不便,也容易对患儿造成损伤。为了改革手术器械,吴守义求助于身边的工人兄弟,并得到了热情的支持。他先后和上海第六手术机械厂、上海工具厂、上钢二厂、上海沪东造船厂等单位合作,联合设计制造出各种适合小儿开刀的手术器械,其中有的还作为产品在全国推广。
年,《美国小儿骨科杂志》主编史秀理来中国开会,慕名要求参观吴守义主持下的医院小儿骨科。当他看到由于条件艰苦,小儿骨科的手术室里居然放着两张开刀床时,不由得十分惊讶——这容易造成患者的交叉感染,是外科手术的大忌。不过,当他从吴教授处了解到,这里开刀手术三千多例,只有一例感染时,才真的震惊了。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术后感染率啊!它得归功于吴守义教授严格的消毒隔离管理制度。
如今,“开刀间里两张床”早已成了在学生中间传诵的故事,年逾八旬的吴守义离开手术台也好久了,甚至连他引以为骄傲的学生都有不少人退休了。但是,那时的制度还在,事业则更其兴旺。
让医院在全国名噪一时的第一个“大事件”,也与抢救工人有关。它发生在建院十周年后不久,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场“难忘的战斗”:
年12月13日,26岁的建筑工人小周在施工时不慎触及伏的高压电,从20米的高处摔到地面,他被急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心跳停止时间至少已18分钟。当时,国内外医学界一致认为,心跳停止超过六分钟,脑细胞就将发生不可逆性损害,心跳停止的时间越长,复苏的难度越大,抢救成功的希望越小。医院的医护人员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考验,大胆地应用了肾上腺素心内注射,伤员的心跳、呼吸相继得以恢复——要知道,当时国内外的教科书上都强调,对电击伤病员忌用肾上腺素。
但病员仍处于深度昏迷中,在施行急救措施后被送入第二军医大学的高压氧舱——当年唯一的高压氧舱——作继续治疗。由医院党总支书记王立本带领的抢救组日夜陪同进舱作加压治疗。神经内科俞丽华,麻醉科金熊元、吴嗣洪,神经外科沈玉成,外科吴生一及内科肾脏组的医务人员不顾多次加压减压对自己身体的影响,始终坚守岗位,密切